“复旦导师制计划”系列讲座之《邂逅历史地理》

葛教授先从历史地理这个学科名讲起,说到它研究的都是至少一代人以前的地理变迁,然后又谈到竺可桢提出的历史地理四个时期——器测、方志、物候、考古。这四个时期分别都是由其研究资料来源命名的,这也体现了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要拿得出证据方可下定论。但证据资料繁多,去伪存真就需要研究者细致入微的分析与见微知著的能力。譬如,从方志中找到的”监镇董楷”一人的头衔便可以说明彼时上海已经建镇,这是上海历史中一个关键点。后来葛教授又说到了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例如上海话在租界时期吸纳了许多英语词汇,”老虎窗“竟然来源于音译”roof“,让同学们大开眼界。介绍了历史地理学的实际应用,比如确定港口位置或计算大楼沉降后,葛教授还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若干问题。
我们上中-复旦导师制计划的学生该有多幸运,才能和葛剑雄教授这样的大师级人物面对面呀。或许复旦的研究生们都不一定能够经常听到葛教授的讲座,而我们却邀请到了葛教授亲临上中为同学们带来这样一场非常有趣却不失学术内涵的讲座。不得不说,这场讲座让同学们受益良多。
“复旦导师制计划”历史系列讲座之《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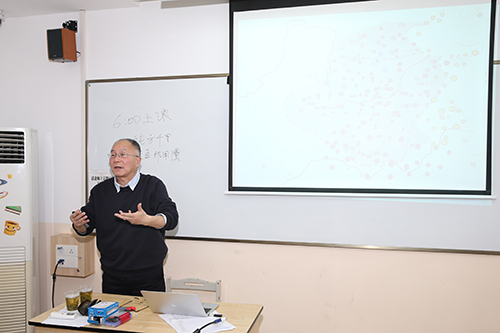
3月3日晚,姚大力教授又一次来到上中,进行历史微课程第2堂课«传统中国的华夏中心观»的讲座。
教授首先举办了清朝官府之例。马格尔尼在乾隆时来到中国广州,给当地官员演示使用每分钟十几发的后膛火枪。当时中国多前膛火枪,两三分钟发一枪。马氏原本希望当地官员能感兴趣,得到商机。谁料那些满大人看完精彩的演示后,面无表情,无动于衷,什么条子都没备,就回去了。
陈独秀在20世纪初回忆说:只有我在21岁以后,我才知道,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也可以显示中国人长期顽固的“天下中国观”
——A.此世界只有一种文明,它注定外化为一个统一之强国;
B.此强国乃天下唯一,而不是均衡多国体系内成员国之一;
C.因此有不同文明文化之人群的差异,乃是统一文明,文化之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也因此,若这个文明经过一个分解为若干国的时期,也常被看成是一国从分裂走向统一进程中的过度或不正常之时期。(时至如今,我国历史叙事也仍然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国家若分裂则必敌对,敌对则必打仗,打仗则人民必颠沛流离,苦不堪言。)
D.故中国有“教化”之责,其他人则有向化之心,教化,向化之最终结局,乃是从汉文明覆盖天下的大同之世。
E.在大同到来之前,实现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联系之主制度框架只有朝贡与册封体制。
五世纪以前,中国认为世界要么只有中国,要么是中国之外那些“四方,四国”的“蛮夷们”;但五世纪以后,尽管四方四国仍处于下导地位,但世界已经将中国与四方,四国融合,形成天下概念。
今天讲的内容较快,教授继续讲下一个章节——«征服和屈服——佛教在汉地的本土化»。征服,是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屈服,也是佛教屈服于中国文化的选择与改适。
佛教初到汉地,经历了诸多困难。于民,佛教首先的征服和屈服,乃是“神仙方术化”,于是,罗汉被描述为“飞行变化,旷劫(很长时间)寿命,住动天地。”而罗汉之下的阿含那,也享有“寿终升神,上十九天。”
第二次,佛教形成了形而上“的玄学化格义佛教”——力求“以够中放,以配外书,为生解之例。”(玄,指的是老庄道家与别的学派混合的学问,比如用老庄思想解释周易。)
“复旦导师制计划”经济系列讲座之《国际金融简介》

3月3日,继上一讲,我们继续介绍国际金融史。首先,老师向我们展示了两张图表,显示了各个大国的GDP随时间的变化,并向我们介绍了“大分叉”,也即1800年中,印两国的衰落。这样的衰落既有政治因素,也有文化因素,但老师让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经济因素。然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商品市场的基本概念;Y-A-K-H-L其中A指技术,K指资源,H指人口,L指土地。这一切构成了商品市场。此外他还提到了宏观金融学的三大市场和四个主体,也即家庭,政府,企业与国外。随后老师讲到了实际GDP,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才可以大幅提高实际GDP,否则老百姓生活质量不会有太大提高。随后,我们由商品市场转入货币市场。货币市场的基本概念有货币量,利率与汇率。为了让我们理解外汇储备,老师列举了中国援建巴基斯坦时用美元和用人民币的不同。随后,通过几个解决金融危机的案例,让我们大概明白了金融行业的主要工作——制定政策,评估风险。其实,金融是以案例为主的学科,这堂课让我具体了解当今世界金融的运作方式,可以说是收益颇丰。
“复旦导师制计划”哲学系列讲座之《人何以为人》

2019年3月3日,张寅老师给哲学课的学生讲授了讲座,名为“人与非人”。简短地回顾了上节课“哲学何为”的主干思路与重要问题后,我们便进入今天的课题。“人”这一概念究竟是如何被界定的?如果一位婴儿出生起便被放逐至原野,被其他动物抚养,他又是否符合“人”这一界定?张寅老师在讲座中做出了解答。
在科学领域,人与非人的界定主要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与其他物种的自然分别,与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分别为当今的两大研究方向。而在哲学领域,老师提到,“人”这一概念遵从于一派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主要观点——认为,人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动物,从属于共同生活。而polis一词,也由此从城邦引向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在这里亚里士多德举了两类反例,认为遗世独立之人,“是鄙夫或是超人(overman)”。这两类人,他们都丧失了人的共同性本质,在历史考证后,亦被证明几乎不存在。故而,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亦是马克思的观点,即人是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动物。从这个重要的观点,老师引申出了很多事关当下的重要哲学问题。这些问题都与人作为社会性存在息息相关。首先,既然亚里士多德派学者认为人之存在必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共同体,那么是否可以认为不同的共同体所包含的人,并非同一种人?这是亚里士多德传统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人类社会的演变中,也自发地形成了一定的地域歧视。而马克思和亚当斯密都认同说,人类应认为自己从属于一个统一的“人类社会”。这样的观点规避了如上问题的,一般描述为“世界主义”。再之,老师提到了“社会角色”的问题。基于人必从属于特定的社会,产生了两个基本的问题——人能否认同自己的角色?以及,一个人的多个角色能否和谐?针对第一个问题,老师提出了在个人承担的角色中,有些角色是潜移默化间被社会给予的。这些潜移默化间形成的角色,又有不易察觉,充分社会性和一般被认为无害的特点。比如说,学术界研究的“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s”便是一例,即现代社会许多民族所标榜的“传统”,实则是现代人在近百年间发明出来的。老师提到十九、二十世纪的日本,大行“武士道”。而“武士道”这一字眼实则在古书目中几乎不怎么出现。这可能便是日本在为军国主义做准备。这种潜移默化间被灌输的“武士道”精神,对二十世纪的日本有着深刻的影响。从个人层面上来讲,社会潜移默化的呼唤,会导致个人的傀儡化或非人划。而人倘若觉醒,又会致使深重的身份认同危机。另外,针对第二个问题,老师还谈到一个人的多重身份可能存在不可忽略的冲突,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以另外一层身份弥补当下身份的认同危机,自古以来便有如此现象。中国古代士大夫有“儒道并行”的情节,他们从修道中得安慰。今天,老师提到,有许多大资本家,敛财时毫不手软,但他们同时又是大慈善家,比如乔治•索罗斯。同时,在现代生活中,也常出现“脱离社会角色的短暂时刻”,来弥补身份冲突的认同危机。老师继而从群体着眼,谈了社会运作中,常常利用如上认同机制而制造的意识形态——制造次等人和罪人。老师提到,在社会内部人为地制造次等人和罪人,引发群体排斥,是重建集体凝聚力的一种有力方式。在西方,曾经出现过大规模而极恐怖的“猎巫运动”。研究发现,“猎巫运动”出现的时间,刚好几乎都是某个群体缺乏向心力,群众涣散的时期。同样地,孔飞力也研究得出,清朝雍正年间也出现过为了加强群体凝聚力,而开展的全国性打击“跳大绳”的运动。被潜移默化地“抹黑”的其他人种,落后大洲的国家和其他信仰的群体,另一个性别,为什么他们会被套上“次等”甚至“罪人”的帽子,这是群体中寻求认同的我们,也需时时提防而思考的。最后,老师还跳开原有的假设,补充了另一派学者的观点,认为人首先是一个动物,首先应许考量其动物性,而后探讨其人性。老师提到,这派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派观点恰为对立。韩非子和霍布斯便是其中的两位支持者。韩非子言“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霍布斯言,“在没有一个共同的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下。”他们的观点概括为,只有在生育控制、生产发达、且其上有一个统治权力的存在下,人才能成为有秩序的,社会性的动物。这些条件,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复旦导师制计划”政治系列讲座之《国家的形成》

3月3日晚,熊易寒老师为我们带来了政治方向的第二节课。
这节课的内容有关国家形成,主角是现代国家。熊老师为我们梳理了现代国家形成的脉络,在回顾历史的同时对当下也有诸多启发。
现代国家——或者说,民族国家——最早起源于15世纪。它的诞生削弱了封建割据和教会力量,强化了中央集权。16世纪的宗教改革,18世纪的欧陆战争,19世纪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20世纪的殖民地独立运动,都是人类走向现代国家过程中的时间。
民族和战争两大概念对现代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民族构成核心凝聚力,战争则提供外部刺激。就民族而言,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建国中的作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最终以“民族自决权”的形式推动了殖民地独立运动。但在当今国际秩序中,“民族自决权”已经不再是一个被公开讨论的话题——很多国家自身是多民族的,如果放任民族主义发展,这些国家就会被撕裂。此外,民族主义是排外的,其意识形态建立在对本民族优越性的先验肯定上。如果不加以控制,民族主义势必会沦为分裂者和极端势力的帮凶。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有助于国家形成,在当代有被抑制,可见其角色是多元的。
就战争而言,熊老师提出欧洲的战争经历了4个阶段:骑士战争,雇佣军战争,常规军战争,民族战争。每一次发展都让国王拥有了更大程度的中央集权,也更加强化了民族国家在人们心中的存在。战争对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很必要的,而民族国家又是最具战斗力的国家类型,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作用。
在介绍完以上内容之后,熊老师又给我们看了一些先贤对国家的分析与评论。马克思、韦伯……哲人的智慧闪烁着光芒,他们的语言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两小时很快过去了,我们的课也结束。所有人都收获满满。我们期待下周的复导。